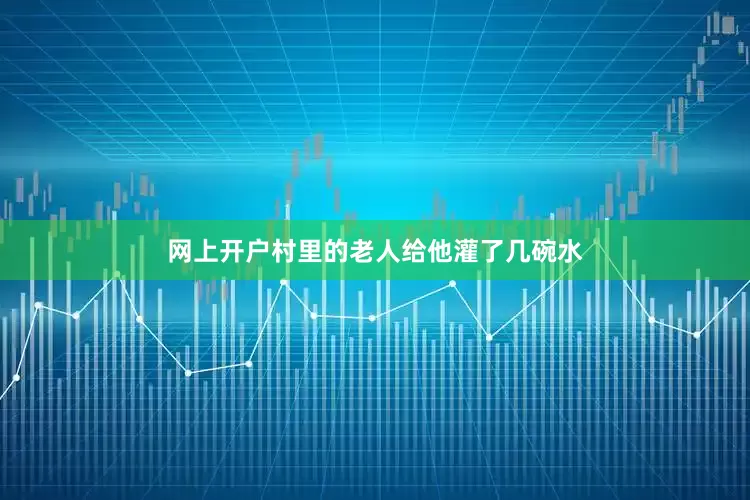
几天前,老表舅在手机上看到一个视频,内容是一个年轻人正在用水桶养殖小球藻。老爷子看见后非常惊讶,忍不住大声说:“这可真是小球藻!现在大家吃穿不愁,怎么还有人折腾这个玩意儿?”话音刚落,老爷子便开始侃起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故事,那时候人们极端饥饿,什么“代食品”都吃过,包括小球藻。老舅的话,在如今丰衣足食的时代,听起来格外令人心头发紧……
根据老爷子的回忆,大约从1958年春天开始,全国各地的粮食产量就像“上天放卫星”一样被吹得天花乱坠。原本每亩地只能产几百斤粮食,最初有人夸大成千斤,后来胆子更大,竟敢报几千斤,最后甚至不说亩产一万八千斤都不好意思开口。当时不仅没有出现粮荒,广播里甚至还有“粮食太多了”的声音,号召大家敞开肚皮多吃饭。号召归号召,可虚报的数字毕竟顶不住真粮食的紧缺。实际上,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,食堂里的饭菜已经越来越少,肚子填不饱还得继续干活,许多人心里充满了怨气。
展开剩余85%那时,村里有人悄悄编了顺口溜:“公社好是好,汤都喝不饱”,“食堂光汤,饿得发慌,干活没劲,吊旦精光”……有趣的是,食堂里的饭菜少得可怜,但广播里每天依然播放着农业丰收的好消息。这让许多人困惑不已:过去农业不发达,粮食不多,好歹还有口饭吃;如今农业发展了,粮食产量增加了,为什么大家反而连口饭都吃不上?当时环境特殊,村干部权威,大家虽然心里有怨气,却没人敢公开说出来。加上信息来源有限,多数人以为粮荒只限于自己村子,广播上天天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,粮荒应该很快就会结束。谁料,这场困难不过是开始,接下来的三年里,粮荒不仅没缓解,反而日益加重。小球藻,便是在1960年年底最严重的饥荒中被推广的。
谈及1960年的情形,老爷子感慨万分,说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时的凄惨景象。他讲述了几件当时发生的事情,让我们自己体会那个年代的艰难。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他同村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老人,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枣儿”。1960年冬天,村里断粮,人人饿得眼冒金星,走路都摇摇晃晃。村附近的草根、树皮几乎被扒得一干二净,只有村中心庙门口的一棵苦楝树没人敢动,树上挂满了苦楝枣。这个“枣儿”实在饿急了,竟然爬上树打了把苦楝枣下来吃。大家都避开这树的果子,因为它又臭又苦,还带毒。
“枣儿”吃了足有一把苦楝枣后,毒倒了。村里人发现他时,他倒在地上口吐白沫,脸色发青,怎么叫都没反应。那时连饭都吃不上,更别说解毒药物了。村里的老人给他灌了几碗水,放到打麦场晾晒,半天都没动静。大家都以为他死了,结果下午他竟然慢慢缓过神来,自己爬起来回家了。虽然接下来的几天他腹泻厉害,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。村里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从此以后,大家少叫他的真名,改叫“楝枣儿”,后来简称“枣儿”,他的真名反倒渐渐被忘了。
上面的故事虽让人难过,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更让人心惊。在最困难的岁月里,一些人死了无法停灵,只能当天草草下葬。没想到第二天早上,家属发现尸体竟被什么东西扒走了。从那以后,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家里人陪着那些没有停灵就下葬的尸体,晚上守护不敢离开,生怕尸体被扒走……
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,小球藻这种“代食品”开始在他们那推广。老爷子说,当年制作小球藻的过程令人难以接受。先用尿液混合水藻种子,放进水缸或池塘里,晒太阳暴晒,等到一定程度,再把水藻从尿液中捞出来消毒,之后才能食用。小球藻的吃法多样,有的和粗粮一起做窝窝,有的做粥,还有的拿来做包子馅儿。但老爷子印象中,虽然宣传说小球藻营养丰富,产量却很低,制作过程又令人难以忍受,所以没人愿意大力推广它。
除了小球藻,老爷子说他们吃过的其他“代食品”更让人震惊。他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个问题:那时候没人打野味、抓鱼吃吗?我也曾问过老爷子这个问题。他听后瞪大眼睛,难以置信地反问: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?”他说:“那时草根、树皮、树叶子都被吃光了,你觉得还能剩下鱼和野味?”老爷子讲,1959年饿得两眼冒绿光的人们几乎把所有能吃的野物都抓得差不多了。至于鱼,基本是公家的鱼塘或水库,有人看守不许靠近。再说1958年打麻雀的时候,大家疯狂捕鸟,到了1959年之后,连鸟都不好抓了。
从1959年开始,广播号召大家夏收秋收后,还要到野地去搞“小夏收”“小秋收”,就是在河堤、路沟等地采野菜、野草。当时大批人马过去,连路沟边的稗草、狗尾草种子都被扒光,哪里还有野味残留?这些草籽被收集起来做窝窝吃。草籽细小难消化,人们后来还想办法先磨碎再吃。野草终究不是主粮,再怎么采摘,几天也吃不饱。为解决吃饭难题,广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“代食品”。
老爷子说,那时他们根本不知道“代食品”是什么意思,只要能填肚子,啥都往嘴里塞。广播把“代食品”分成四类。第一类是平时不吃的农作物剩余物。老爷子印象深刻的是麦秸粉做的馒头、麦糠做的窝窝。平时麦秸和麦糠都是喂牲口的,谁吃过人吃的?广播说麦秸馒头和白面馒头差不多,但相信的人很少。可不管信不信,填饱肚子是真的,大家最后还是吃了。麦秸和麦糠难消化,尤其是麦糠,吃时味苦难咽,拉时更难受。还有玉米皮和玉米秸,本是喂牲口的,也被磨碎用来充饥。老爷子还记得一个关于玉米皮馍的顺口溜:“大跃进,喜事多,玉米皮做出优质馍,不仅香甜又美口,营养价值真不错!”他至今不懂玉米皮有没有营养,但味道像嚼蜡,吃一嘴都是渣渣,难吃还难拉。
第二类是野菜野味。老人骄傲地说,想知道一个人是否经历过那些苦日子,随便指一种草问他能不能吃就知道了。那时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,几乎尝试了所有能吃的花鸟鱼虫。最受欢迎的是榆树,因为榆树春天结榆钱,夏天叶子能做窝窝,秋天还能扒树皮磨粉吃。可以说,榆树在饥荒年代是“全能树”。此外,野苋菜、洋槐叶、沙枣、野枸杞等野生植物也都被列入食谱。那个年代不讲口感,只要不毒死就行。即使是有毒植物,只要知道怎么处理毒素,也会被拿来吃。这种吃法风险很大,误食或处理不当常造成悲剧。老爷子说他们村有位老太太从树上摘木耳煮给家人吃,为防中毒她先自己尝了点,结果她没事,婆婆、丈夫和两个孩子却都被毒死了。她年轻时哭着让村干部抓她,判死刑,但村干部知道她不是故意的,也懒得费事,就劝她别想太多。她孤身活到八十多岁,算是福还是祸没人知道。
第三类就是前面提到的小球藻、水藻一类。老爷子说广播上鼓励吃,但现实中没啥用。水草虽然看起来一大坨,一出水就缩水,根本顶不饿。
第四类才是真正的“食品”,是合成食品,比如豆制“人造肉”、植物提取的“叶蛋白”等。这类“代食品”口感好,营养高,还象征身份。那年代能吃得起的不是普通老百姓,有时拿这些比拿钱还管用。这些“高端产品”在最困难的年月,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。
最后,老爷子依然不明白,为什么如今衣食无忧的时代,还有人搞小球藻吃。他对现代年轻人的许多焦虑和习惯直言不解。在他记忆中,现在年轻人的思维与他们那个年代完全相反。比如他们视为珍宝的人造肉和叶蛋白,如今却被称作“合成食品”,归类为廉价低级货。如今社会追求“绿色食品”,不打农药不施化肥,老爷子觉得很有趣。以他的印象,不打农药不上化肥的农作物产量至少低三分之二,外形和卖相也差。年轻时,只有打了农药上了化肥的农产品才值钱,少打药少施肥的都算“残次品”,没人要。那时候农产品个头大颗粒饱满才抢手,现在倒好,买菜要虫子咬过,买馒头要发黑的,还说那才健康。对此老爷子哭笑不得,他说以前连吃不上打农药化肥的农产品能活到七十岁的老人,一个村也没几个。现在吃了那么多年药肥农产品,活到八九十岁的倒不少。他总结现在的焦虑一句话:“还是吃得太饱太好了,饿几天,啥都能吃!”
发布于:天津市启恒配资-国内十大炒股杠杆平台-厦门股票配资开户-配资平台买卖股票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